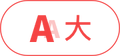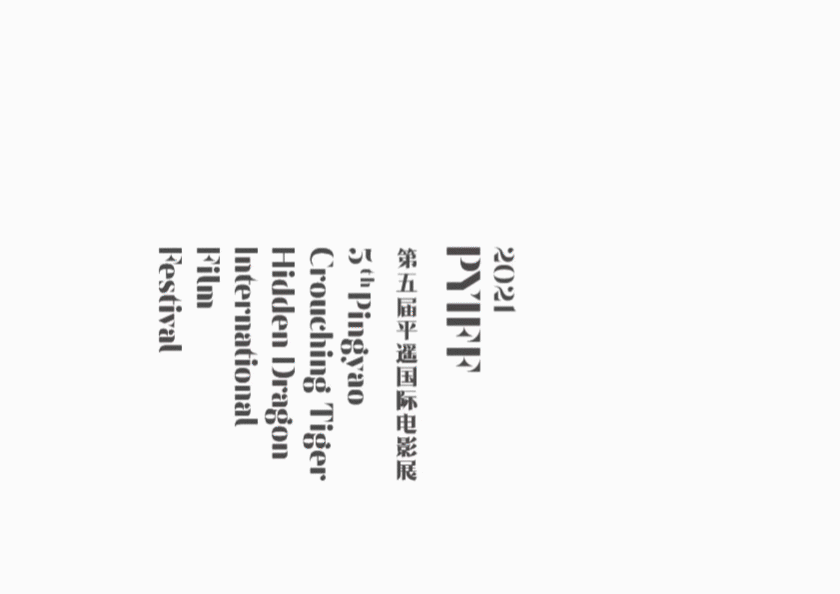
【对话Dialogue】
在山西生活、学习、创作
时间:10月19日 10:00-11:30
地点: 平遥电影宫·站台
主持:王晶(导演,代表作《不止不休》)
嘉宾:毕赣(导演、编剧,代表作《路边野餐》《地球最后的夜晚》)
大飞(导演、编剧,代表作《异乡来客》《残香无痕》)
韩杰(导演、编剧,制片人,代表作《Hello!树先生》《解忧杂货铺》)
贾樟柯(导演、编剧、制片人,代表作《三峡好人》《山河故人》)
李睿珺(导演,编剧,代表作《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
宁浩(导演,代表作《疯狂的石头》《无人区》)
袁媛(导演,编剧,代表作《滚蛋吧!肿瘤君 》《明天会好的》)
语言:中文
主持(王晶):
辛苦大家一大早来这边,在寒风中参加这次论坛。我叫王晶,今天客串一下主持人,今天论坛有个非常有趣的主题,在山西生活、学习和创作的电影人。
先掌声有请各位,贾樟柯导演、宁浩导演,他们也是两位新晋男演员;李睿珺导演、毕赣导演,他们两位在山西完成了电影学习,电影之路从山西开始;还有袁媛导演、大飞导演和韩杰导演,欢迎。
刚刚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袁媛导演还在说,千万别问我山西话,千万别让我说山西话,她说我不会说山西话。我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也在想,其实电影这个事情跟生活有关,生活和创作永远分不开。我自己个人的感受是,当你进入创作状态的时候,很多创作者需要寻找一种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从哪儿来?我觉得是从你的生活经历里来,是从你怎么一路成长过来来的,所以回看故乡,或者回看你成长的经历,其实对于一个创作者是非常重要的。今天也想请各位聊聊家常,聊聊创作。
先请贾导说一说,昨天晚上我们电影展的平遥之夜有一部短片《地球最后的导演》是宁浩导演和贾导一起主演的,里面有一幕,贾导在自己房间打开一本书认真阅读着,说这本书写得真好,这本书叫《贾想》。提个假设性问题,如果有一天您要拍一个关于自己的电影,那个电影的的开场会是什么样子?在什么地方发生?跟什么人有关系?
2021PYIFF学术活动【对话】在山西生活、学习、创作-导演王晶
贾樟柯: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平遥国际电影展,今天天气有点冷,不过太阳出来了,估计一会儿会好一点,大家辛苦了。我在山西已经生活了50年,这个论题本身也跟今年咱们山西挂牌建设了山西传媒学院山西电影学院有关,我们在座的几位,大部分都是山西传媒学院山西电影学院的教师,这是一重身份。再一重身份,我们都跟山西有关。我是土生土长的山西汾阳人。大飞是山西岢岚人,他是山西传媒学院五龙口时代优秀的毕业生。大飞的电影《异乡来客》也入围了今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下个月就展映了,他也是我们山西传媒学院山西电影学院的老师。
袁媛是《滚蛋吧!肿瘤君》的编剧,她自己导演的作品《明天会好的》去年跟观众在电影院里见面了,她既是编剧又是导演。
韩杰导演是山西孝义人,我的吕梁老乡,他的处女作叫《赖小子》,就是在孝义拍摄的,后来又有《Hello!树先生》,还有《解忧杂货店》等几部影片。他是一位编剧,也是一位导演,他的作品都是他自己编剧的。
毕赣导演是山西传媒学院的毕业生,他是贵州人,在山西传媒学院度过了他的大学时光,他的第一部作品《路边野餐》有很多山西传媒学院的老师和同学参与制作。
李睿珺导演是甘肃人,也是山西传媒学院的毕业生。宁浩导演是山西太原人,具体来说是尖草坪那边的人,他的第一部影片《香火》也是在怀仁拍摄的,之后他辗转全国。王晶导演也是太原人,处女作《不止不休》去年在平遥国际电影展公映。大家身上有山西背景的经历,又都是山西传媒学院山西电影学院的老师,除了韩杰导演(韩杰导演即将成为山西传媒学院山西电影学院的老师)。
在山西工作、学习、创作,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回到主持人说的,如果拍山西的电影我会以什么场景开始?场景空间就很多了,作为山西人的儿子,我23岁离开山西,但是生活习惯,特别是思维模式一直是一个山西人的模式,除了电影中使用自己的语言之外,我记得我们在有一次给宁浩导演拍小片的时候,他说的一个观点我特别认同,他说他的思维方法、情感方法是山西人的,这一点贯穿了我们几个人的创作,是改不了的东西,因为骨子里面就是这么一个人,成长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如果说要选择一个场景,可能它是一辆从太原开往黄河边的公共汽车,里面各色人等上上下下,也可能是我的家里面,我远道回来,父母在炒菜,我觉得那是我们家庭生活最动人的时刻,空气里面弥漫着醋味跟汾酒的味道,厨房里面炒菜的烟飘散在房间里面,一家人其乐融融。山西人是非常讲究和看重生活的,家庭生活、家庭观念,很恋家,这个电影会从家出发。
2021PYIFF学术活动【对话】在山西生活、学习、创作-导演贾樟柯
主持(王晶):
我顺着贾导刚刚在谈的问题问一下宁浩导演。我听身边一个朋友说起过,您十多岁的时候就有过一次离开太原去北京的经历,好像是跟父亲很认真地谈过我想去北京了,应该是在很小的时候。
宁浩:20。
主持(王晶):当时您是很想离开这个地方吗,当时的出发点是什么?
宁浩:
出发点就是上学,那个时候老贾还没有把电影学院搞好,所以就得去读书。我当时是在太原话剧团上班,每天早上起来的工作就是打白开水给书记送到房间,然后回来就写板报,没有什么特别认真的创作工作。好不容易有一个话剧,我记得当时我们演完,台上有30多个演员,台下有十几个观众,话剧在那样一个状态下,完全没有人看。
其实还是希望年轻人能够有一些更好的接近艺术和创作的事情,所以当时比较活跃的学习的地方还是要到北京去,所以就选择了去北京读书。
主持(王晶):
您的电影里其实没有很多时候把场景或者是人物放在山西这个地方,就像刚刚贾导说的,他觉得你们聊天会提到山西的人有一种独特的性格或者是把这个性格体现在我们作品里面。我挺好奇那个性格是什么样的,或者你怎么归纳那个东西?
2021PYIFF学术活动【对话】在山西生活、学习、创作-导演宁浩
宁浩:
我有一个习惯,我创作的时候是自己写剧本,人物一定是自己过的,但是自己 写的时候我发现,我得把人物的台词都拿山西话说一遍,如果那个里面变成太原话的方式,我就特别理解这个人物,普通话的方式从我自己的出发点来看就没有那么通,这个导致很多演员在跟我合作的时候刚开始是不适应的,他说为什么这么说话,语序结构是这么讲,尤其我跟徐峥拍《无人区》的时候掰扯好多台词,他不太理解,因为他是上海人。反正他在加油站里头跟老板是冲突的关系,说话的方式,我记得我是完全拿太原人的处理办法去写的,他就很不理解。最后他也只能说好吧,我听你的,你是导演,就按这来吧。
所以有一些人觉得我拍的第一部电影里面是重庆人,很多人说你是重庆人吧,我说不是,那里面很多人物写的都是山西人,因为它很有我熟悉的、周围的那些人的性格,才能发生这样的故事,这是我自己的创作体验。
主持(王晶):请大家都说一说。刚刚贾导提到李睿珺导演、毕赣导演他们其实不是在山西长大,但是他们很重要地接受电影教育或者大学时光是在咱们太原度过的。甘肃和贵州我都去过,我的感受是,甘肃和山西还是或多或少有相似的地方的,饮食、人的状态,城市的地貌,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从你的角度还是有不一样的,所以我想听睿珺导演说一说怎么看山西,从他的角度。
2021PYIFF学术活动【对话】在山西生活、学习、创作-导演李睿珺
李睿珺:
因为上大学,我才第一次离开甘肃、到了一个甘肃以外的第一个城市,这是我长这么大以来离开甘肃到的第一个城市,就是因为来山西上学,它也是我(开始)接触这个世界,或者对中国有一个不一样的了解。然后你第一次听到了本省以外的另外一种语言,你见到了跟你们看似相似但是又有差异的一个地域的地貌,包括人、生活方式。但是有一点共通的,就是我们都是以吃面食为主的。
我对电影的认识和理解都是从山西开始的。其实我来山西上学是个偶然,因为原来高中画画,本来是想要去西安读美院,但是老师就建议我们多一种选择,然后可以来试试,结果一试就考上了,考上之后就觉得想来上,来了之后其实一开始考这个并没有想过未来要成为一个导演或者做电影人,因为我是画画,其实我考的是影视广告专业,它必须要考美术,是因为这个先天优势考到这边。
考到学校以后,老师上视听语言课,开始接触大量的电影,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们那个地方通电比较晚,我83年的,差不多90年左右才有电,之前都是看露天电影,后来有电视,偶尔放一点电影,也有外国电影,都是配过音的那种,你就很不喜欢,跟你有什么关系。是到了山传之后上学,老师拿一些国外的电影给你看的时候,突然间觉得,它跟你认为的国外电影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看《偷自行车的人》,你就觉得那对父子的命运,看完之后觉得这两个人住在你心里面了,你会反思为什么他会住在你心里面,其实是一个你没有去过的地方,你没见过的人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两个人的遭遇它深深地留在了你的心里面,然后你要为他们去担忧,一下子就会觉得发现了那个电影的另外的一种魅力。所以说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未来想要做电影。
所以山西是我电影启蒙的开始,也是你第一次离开你家乡去接触的另外一个领域或者一个区域的开始,以至于从山西毕业之后,因为想要做电影再去到北京,其实它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像一个台阶把你送到了你想抵达的地方。山西是个很重要的中转站,它让你储备了足够的能量,让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主持(王晶):当时除了在山西认识到电影是什么样的,会有很多山西的朋友吗,这些东西会不会对你的生活和创作有影响?
李睿珺:当然会有,我的同学里基本可能有一半是山西同学,跟他们打交道,甚至比如说毕业之后这些同学也依次去了北京、去了上海,其实他们变成了你未来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你去任何一个城市出差,你都可能会给同学打个电话,可能见到的还是你山西的这些同学,他们可能也离开了山西在别的城市工作生活,但是整体还是那样的一个方式。
主持(王晶):其实这个城市或者地域提供给我们的,最后还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李睿珺:对。
主持(王晶):毕赣导演在山西吃不着辣这个事儿难受吗?
2021PYIFF学术活动【对话】在山西生活、学习、创作-导演毕赣
毕赣:
一开始在学校读书最难受的就是吃饭的问题,毕业之前那三年就没好好吃,但毕了业以后还觉得挺好吃的,人就是这么矛盾的。就像我一直觉得去学校读书是我18岁之前都生活在凯里,特别想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因为我很羡慕我的同学都能住校,能够有自己的宿舍,我每天都得回家,所以我就选了一个特别远的地方,然后就来太原。一来太原就觉得贵州太好了,因为气候太好了。等三年毕业了以后就觉得太原也挺好的。 所以人都是这样,每次要离开了就觉得那个地方会特别好。
主持(王晶):我只言片语听到过一些你当时在学校完成学习以后要拍《路边野餐》的时候,学校这边的老师也给了很多支持,分享一些那个时候的经历。
毕赣:
对,当时要拍自己的第一部电影,每个人的第一部电影都很难,当时我就想说,我特别觊觎我们学校刚刚到货的一台艾丽莎机器,然后就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跟学校的各种老师、领导沟通了,结果 学校就很大方 地 把那个机器送到了贵州。那台机器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因为电影成像品质会好很多,那是我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情,因为那是学校第一台那样的机器,当时学校对我们的整个创作是特别愿意去支持的,包括我的很多老师, 我拍完短片以后我跟我的老师说 , 我准备拍第一部电影了,老师说 , 需要钱的时候给我打电话 , 虽然我也没多少钱。
主持(王晶):他也是后续一直带给你支持和影响。
毕赣:对,直到现在回到太原,上次去学校的时候都挺感触的,见到老师们都觉得很亲切。
主持(王晶):下一部影片里面可以加一些山西的元素进去。
毕赣:下一步再去学校要一下机器。
主持(王晶):
谢谢毕赣导演。韩杰导演,其实我第一次完整地接触电影是跟韩杰导演一起工作,在拍《Hello!树先生》的时候,我帮韩杰导演做副导演。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们在东北已经开始筹备了,当时韩杰导演带着宝强哥从山西到东北,算是进组。然后我说你们去山西干嘛了?他说带着宝强哥去山西体验生活加见人物原型,我当时读那个剧本的时候没有觉得是有人物原型的,整个拍摄中一直在看宝强哥找各种细节,生动地复原他见到的人物原型身上小的细节,小的特质,所以我一直好奇那个人物原型是什么样的,所以电影拍完了也上映了,我还没有见过那个人物原型,今天借这个机会请韩杰导演说说,当时这个人对你的影响是什么样的,他一定是你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很多年的朋友。
2021PYIFF学术活动【对话】在山西生活、学习、创作-导演韩杰
韩杰:
我的第一部是在我的老家孝义拍的,拍的一帮青少年,有上学的,有从学校辍学的,两批孩子的的青少年犯罪、青少年早恋的故事,属于青春犯罪题材的一个类型化探索。拍完这个电影之后,在老家比较传统的民风当中引起了激烈的反响,就认为是伤风败俗,尤其是青少年早恋,还有杀人放火这样出格的行为。
所以在《赖小子》之后,我其实是发现自己冒犯了一个熟悉的地方,然后你又不能为它做出什么解释,因为这个东西解释没有道理的。到了《Hello!树先生》的时候,我还有一个内在的驱动力,还是想写一个我对山西故乡的感受,基于那个时代,疯狂开采煤矿导致的后续的影响。如果说《赖小子》是一个讲青少年在经济开放导致人心变得疯狂的那个年代的故事的话,到了《Hello!树先生》,就变成了另一个故事:煤炭业导致、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烈的社会变动,就是城市化运动,很多农民搬到城里住。《Hello!树先生》从内在上也是在写山西故事,我从情感上一直没有剥离这个东西。
但是基于第一部的拍摄情况,到了《Hello!树先生》,我就考虑,不能在老家拍了,这是非常矛盾也很伤感的选择。最后就把《Hello!树先生》放到一个覆盖着冰雪的东北大地上拍,变成一个黑土地的故事,这也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在情感上,我又只能说依托于、寄希望于人物的诠释,所以带着王宝强又回到太原,回到孝义,深入地看看煤矿业的现状,看看跟煤矿相关的这些居民他们在当地是怎么生活的。人物原型是有一个模糊的原型,其实也不全,这个原型也来自于电影史上卓别林带给我的一种强烈的喜好,还有当年网络生态当中出现的“犀利哥”形象,大体上融合了三种人物形象产生的。不管怎么说,还是我对山西基于时代、基于个人经历的这种感受一直有强烈的表达欲望。所以《Hello!树先生》虽然在东北拍摄,内核还是山西。
主持(王晶):请您多讲讲刚才说的矛盾,这个故事,这个情感的基础都是源自于山西的,你又想离开山西到东北把这个故事完成,那个矛盾是好的还是(怎样的)?
韩杰:
你爱这个故乡,但是这个故乡也有一些社会病灶,大概80年开始,疯狂的山西煤炭业造成了很多人道德上的混乱,包括家庭伦理严重的破坏,城市化的变迁。所以我其实是既想表达故乡对他人生活的关照,又不忍心把这个病灶说出来,非常矛盾,最后还是选择说,那我就换一个地方讲吧。 其实是同根的,在东北其实也一样,也是同样的一个社会现状,全中国都在城市化,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大的社会命题 。
主持(王晶):其实对故土爱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
韩杰:对。
主持(王晶):谢谢,袁媛导演用山西话回答行吗?
2021PYIFF学术活动【对话】在山西生活、学习、创作-导演袁媛
袁媛:
太为难我了,我其实不是在大同长大的,我是在大同下面的一个县出生的,我长到三岁的时候就离开,因为父亲当时已经复员——他年轻的时候出去当兵,当了很长时间的兵,终于复员了,被分配到一个油田,又从江汉油田又去会战,去了中原油田。中原油田在河南省濮阳市,所以我的从三岁一直到高中毕业的这一段时间都是在河南,就是中原的这片土地上成长的。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像油田这种系统,虽然在河南土地上,但它又不完全是由河南人构成,里面什么样的人,天南海北的人都有。
所以我们那个系统里成长出来的孩子,普遍都会有一种身份认同的错位感,他知道他的故乡不在这里,他们都是来自全国天南海北,他又在这里长大,但是河南也不是他的故乡。我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大家其实都没有一个很强烈的的感觉,我将来要生活在哪里、哪里是我的故乡的感觉,基本能去大城市发展的,就去大城市安定下来,要么能跑到海外的就跑到海外去了,大家都有这种漂泊感。对我自己来说,我自己也是漂泊感很重的人,我每到一个城市的时候,都在幻想着说,这个城市会不会适合我生活,我可不可以在这里定居。其实,到现在也没有特别强烈地说,哪个地方可以成为我“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感觉。
我去年的时候,我的父母才完全回到山西他们的老家,他们特别愿意还在他们出生成长的那个村庄,估计是就打算在那儿养老了。实际上,我去年回去之后看了他们的生活条件,肯定是比县城、城市,比他们之前的生活条件要差很多的,厕所就不必说了,直到今年厕所才有了房顶。
我就很感慨。我会觉得挺奇怪的,为什么他们到了这个年纪还要想回到自己已经离开四、五十年的这么一个地方,但是我又觉得这可能就是所谓“落叶归根,故土难离”的心绪吧。其实我非常感激我的父亲,我在青春期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是跟他“斗争”的,因为自己特别想做电影这一行,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做,自己莽莽撞撞这么多年,终于做出一点小小的成就,他其实完全不了解我在做什么,他只知道你的生活是可以自理了,他就觉得比较放心了,他就不再像过去一样,就是不停地想要你考虑一下未来,你的工作不稳定,你的收入不稳定,你以后怎么办?他已经放下这个执念了。
等到我回到家乡的时候,我见到那些有血缘关系但几乎是完全陌生的亲戚们的时候,我才突然有一种特别感激我父亲的心理。如果他当年没有出去当兵,没有离开了他出生的这个地方的话,我今年41岁,我可能在那儿已经当奶奶了。所以在这个点上,我突然一下子跟我父亲之间以前的一些矛盾(就消解了),也可能是因为年龄大了吧,我们两个才开始慢慢的有一些交流,平常的时候,我和他几乎没有什么可交流的东西,因为一说话可能就针锋相对,生活层面、家庭层面,各种各样的矛盾丛生。但是他回山西的这两年,我作为女儿不得不在节假日,在平常没有事儿的时候要回到我的第一故乡去看他们,我才真正地开始了解这片土地,了解我出生的这个地方原来是这个样子,它的景色,我三岁离开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记忆,才开始慢慢地有一点,好像我特别朦胧的记忆才开始复苏。
今年贾樟柯导演突然说,要不要来山西传媒学院山西电影学院做一名老师的时候,我很快就答应了,因为我突然觉得,我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也抱着特别想重新认识故乡的想法。我虽然出门的时候经常跟别人说我是山西人,但是别人一跟我说起山西什么什么的时候,我其实都不知道。有一次遇到杨超导演,杨超导演是河南信阳人,我跟他说我生在山西长在河南,他说你是山西人,你们山西特别好。我就愣了一下,我就问他哪儿好了?他就开始跟我讲,他虽然是河南人,但他对山西的古建筑、对山西文物很有研究,他会花很长的时间定期制定一条线路来到山西,跑到那些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考察古代的寺庙,我才开始明白。我除了知道大同的云冈石窟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古建筑之外,其他我其实对山西几乎是一个一无所知的状态。所以我就想, 通过在 山西传媒学院 山西电影学院 做老师的这几年 , 我可以有一个重新认识、重新 发现山西的一个过程,重新变成一个真正的山西人 。
主持(王晶):
欢迎袁媛导演好好学习山西话。大飞导演的第一部影片我看过,他把它放在乡村,我不知道是不是在你家乡拍摄的,就是在你家乡岢岚拍摄的是吧?大飞导演的视点挺不一样的,我们差不多是同辈人,可能因为他的乡村成长经历,您的第二部影片还是拍摄乡村题材吗?
大飞:第二部影片放到县城了。
主持(王晶):前两天我看贾导的一个采访,他说到,他们(那一代)有很强烈的乡村经验,他觉得(到了)再年轻一点的创作者,可能就没有乡村经验了。我们在城市生活、城市长大,对于乡村的概念很模糊了。您一直在试点乡村这个地方,您怎么看这个东西?
2021PYIFF学术活动【对话】在山西生活、学习、创作-导演大飞
大飞:
比我小一点的,像我弟弟他们,大概已经到了县城里面生活了。因为我们的教育的问题,村校已经全部撤销,全部到县城里去了,导致所有的青年人都带着孩子去县城里面生活了,农村基本就剩下一些孤寡老人了。在这个情况下,以后的年轻人对于乡村的生活会离得越来越远。我觉得自己还有很真实的(乡村)经验,越往后走,对它的记忆会慢慢流失、会消散。在我们国家里面,农村肯定是更广袤的一块土地,我觉得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生活也该被铭记。
主持(王晶):
我很感兴趣,第二部讲县城里发生的故事,会跟第一部有延续性吗?
大飞:
其实没有延续性。第二部的创作初衷是,我特别想去探讨一下当代的时代敏感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心的“距离”,这个是我这次探讨的一个主题。
主持(王晶):
明白,期待看到这部影片。每个导演都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创作过程,我想尽量把时间多留给大家在台下的年轻人,或者是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有40分钟时间可以跟各位导演热烈交流,大家有没有想问的问题?随时可以举手。
提问
毕赣导演您好,我非常喜欢您的作品,同时我也是一个太原人,也即将去到山传。我想问您在创作作品的时候,包括《路边野餐》和《地球最后的夜晚》,您是如何看待您作品中的表达欲。也许您也曾迷失过,如何最后发掘自己想表达的想法以及自己想创作的东西?
毕赣:
我觉得表达欲这个东西每个人都有,就看它是不是用在电影上,刚好我就用在了电影上,感觉接下来你也会用在电影上,去山传好好学习。
提问
请问贾樟柯导演,我非常喜欢您的电影,您对纪录片中的纪实性与虚构性是怎么看待的?比如说您在《二十四城记》当中就使用了虚构性这一手法,您对纪录片中的虚构性与纪实性的看法。
贾樟柯:
我先不回答你这个问题。刚才听了诸位讲的这些事儿,我们青少年的事儿就历历在目了。我们今天主题是“在山西生活、学习、创作”,让我想起,我有过一段去北京电影学院读书之前,一段大概两三年在太原生活的经历,那一段时间我很少向人提及,那段时间对我的成长非常重要。那段时间对一个人来说,那可以说是我到目前为止最困难的阶段,十八九岁高考没考上大学,那就面临生活的选择,你是去就业还是复读,你得找一个出路,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找一个出路,那个时候摆在面前就是未来怎么办,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时候我父亲让我去学美术,因为我数学不好,那时候考美术院校不用考数学,这样的话就去太原学画。
那段生活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方面,你假装好像是在学一门艺术,实际上那是放飞自我的非常重要的三年。因为没有父母管了,第一次出门远行,太原这个城市,那个时候虽然资源不是很丰富,但是它非常可贵的可能在极少的资源里,你要捕捉到那些重要的信息。这些信息可能一年发生几次,但是对一个处于成长阶段的年轻人来说非常重要。
我记得有几个东西对我是重要的,有一个东西是有一年,突然有一个摇滚音乐会在太原体育馆举办。那时候对摇滚音乐也没什么概念,反正感觉就是大城市年轻人很喜欢,我就买了一张票去看了。那个乐队有唐朝乐队、黑豹乐队,那是我第一次在现场听摇滚乐,是在体育馆,非常激动。太原那个时候并没有太多摇滚乐,但是这一场演出,我想可能跟天天有摇滚乐听的城市的孩子不太一样,因为你好像捕捉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它是一个崭新的东西,虽然它一闪而过只是两个小时的演出, 但是它会在我心里有长久的 回响 ,那种精神就注入到你的身体里。
另外一个我好几次也讲到,我非常感谢省政府附近那个外文书店,不知道这个书店现在还有没有。外文书店二楼那个时候有进口图书,主要是画册,有梵高的,有印象派,有西方的各种各样的进口的画册。那些画册在当时都非常昂贵,我们做学生的根本买不起。但是那个书店有个规矩,在那些画册旁边放了一双白手套,你戴了手套就可以看,看一下午都可以,我就是那个画册的读者,我戴着那个白手套站在外文书店,每到周末就去看那些印刷品。不像北京有很多美术馆、有很多国外的展览,但是就是那样一个小小的窗口,对一个县城来的孩子来说,其实已经打开一片天地,在那儿接触了西方的美术。
另外一方面,我最早的短片筹措资金时,很多资金就来源于我学美术时候的山西同学,因为他们有一技之长。像我们平遥国际电影展的联合创办人,现在山西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王怀宇先生,他跟我就是学画时候的同学,他比我早考上大学。他们考上大学之后,因为会画画,能赚一些外快,给人家画个广告赚了一些钱,其中有很多就补贴到我的电影里面。我们的友谊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缔结的。
我觉得山西人,我们讲乡谊、同学之情。我对我们山西的人情社会非常留恋,也非常保持距离,这是一个矛盾体。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几位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我们身处其中有时候不堪重负,有时候又觉得它是我们生活全部的支撑,可能这种矛盾就伴随着每一个山西人的生活跟创作。我也不是怀念(自己最初起步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时代在进步,现在大家通过网络,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多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太原作为一个中型城市,作为一个省会城市,它非常珍贵的一些一闪而过的那些文化信息,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非常重要。所以这也是后来我自己办平遥国际电影展(的原因),包括我们在汾阳还有一个短片周,为什么要把一个电影展选址选在一个县城里面,平遥县只有50万人,是因为我经历过那样的生活,我知道那些资源对于家乡来说有多重要。它也形成我后来做很多事情的一种逻辑,因为你的情感毕竟在这儿。
今天这个座谈也让我想起,我第一次见宁浩的时候,我也很小,他就更小了,他是乐队的成员,他是一个摇滚乐手。我非常想哪一天宁浩的乐队可以再演出一场,就在我们平遥国际电影展,排练一下。
主持(王晶):我们预定一下明年的开场表演。
贾樟柯:
他也是一个热爱摇滚乐、热爱艺术(的人),他也学美术,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虽然非常零散、片段,我也知道宁浩还在酒吧驻唱过,而这个酒吧的老板就是平遥电影宫的设计者廉毅锐,大家就是有这样一种机缘,非常有趣。但是今天回忆起来,它就是我们最初的艺术生活。我觉得今天讲起来就是,如果你要从事艺术工作,首先得有艺术生活,所谓艺术生活就是去听摇滚乐,去看画展,去看话剧,去拍电影,去拍短片,去看电影,去听讲座。我很感谢那几年在太原的这样一个环境,人们常常会抱怨说,我们好像文化活动比较少,好像没有中心城市北京那么丰富,那确实有这个问题;但是同时它又不是没有,它也有,在那样的环境里它让我觉得倍感珍惜。
关于纪录片跟虚构——我刚才乱发挥了一通,因为我怕忘,年纪大了老怕忘事情——刚才我提到了摇滚乐,后来我们在太原铁路局有个体育场,又看了崔健的摇滚乐演出,这些真的很重要,因为它形成了你成长过程中的一种叛逆,一种不安于现状,一种尝试新东西的这样一个思维模式。纪实与虚构,纪录与剧情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延续了这种精神,艺术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绝对的说剧情片就不能有纪实、纪录的成分,纪录片就不能有虚构的成分。我觉得最终大家通往的都是同样一个目的地,就是艺术的真实,什么手段都可以用,就好像摇滚乐一样,你可以吼叫,你可以唱,你可以抒情,你可以一句话不唱,就演奏,我觉得内在的就是这样一个打破界限的、自由的意识。
主持(王晶):
我刚才跟宁浩导演简单八卦了一下,听说你们年轻时候这帮摇滚乐的伙伴们现在也在身边工作,我听说贝斯手郭志荣老师还在台下坐着,你们乐队叫什么名字?
宁浩:
我们乐队这个名字非常有趣,每次都被歌手郝云取笑,他说今天台下来了一个导演,他过去搞了一支乐队,但是他们那个年代取名字呢,他们肯定觉得很先锋,他们起了个名字叫“同志乐队”。
主持(王晶):那会儿是怎么想到要做乐队?
宁浩:
我觉得老贾刚才说得特别好,他很细腻地把我拽回到当时的时代里,有很多细节,他说了体育馆的摇滚乐演出,我们都有印象,他说的这些事件都发生过。就像昨天我跟韩杰导演聊起来的时候,他说他之前在文源巷开过租赁店,开过租录像带的店。我们昨天还聊起来说,文源巷当时算是一个文化中心了吧,基本上这边都是卖乐器的,卖打口碟,廉毅锐的酒吧是在那边。
主持(王晶):在37中对面。
宁浩:
对,就在一条街上,所以基本上那是一个文艺最活跃的地方,就是排演场。好像这些搞文艺的人都会喜欢去那一带,在琴行坐一坐,晚上到酒吧坐一坐,聚在一起玩玩乐器。那个时代就是像这样的地方和这些事情,就是一些卖打口碟的小店,在支撑着这些其实还是蛮荒芜的一块文化土地上的一些人的希望。所以因为有这样一件一件的东西,才能和这样的地方,才能让这些人一步一步走进电影或者艺术的道路,虽然也会很曲折, 有的人是去做乐队了,有的人去画画,无论怎样 , 最终都还能坚持在这条路上。
而且我也在想,现在这个时代又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当抖音这些新的记录技术和影像技术又开始普及,所有的影像权力完全稀释,完全平均化,在这样一个民主化的过程里面,作为一个传统的电影手艺人他应该怎么办,或者做什么样的东西才是大家愿意看的。其实从我个人的思考来说,可能要越来越靠向个体,从我个人的思考来说,你要越来越靠向个体和个体的认知,那么就无法摆脱开“你从哪里来”的问题。
其实我后面在写一部电影就叫《太原往事》,我也只能够把回到对自己的研究和过去的生活,我觉得那个部分才可能是唯一在这个时代有价值,能够提供出来的东西,在我个人角度来看是这样的。
主持(王晶):
其实宁浩导演刚刚最后说的这一段是回答了第一个观众的问题,就是怎么开始创作。其实可能每一个创作者在某一个阶段会试图往自己内心去看,看自己,它那个是带给你力量和独特性最大的东西。
我分享一点小的个人感受,我可能没有跟贾导说过,我第一次在电影院看您的电影,其实是《世界》在电影院上映的时候。我觉得电影这个东西一定是私人性的,影片中有一个镜头,我当时看到那个镜头的时候,我整个人被钉在电影 院的椅 子上,就是有一个从北京开往山西的大巴车,您拍了一个空镜头,对着车窗前面的高速路,长长的一个空镜头。那个东西为什么击中我,我不知道贾导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一直坐大巴往返于北京,往返于汾阳或者太原之间。我个人其实有段时间也是一直在往返北京,像宁浩导演说的,太原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养分,没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我们想吸收新的东西,我有一段时间会经常跑北京看小剧场话剧,看演出什么的。所以那会儿都是周五坐一个大巴车到北京买一个话剧票,然后周六或者周天回来要上学,然后我再坐大巴车回来,高速公路记忆一直根植在我那段成长经历里面。当我看到贾导电影里面出现了一个我那么熟悉的场景的时候,我整个人被钉在那个地方了。 我觉得是一个作者把自己私人的内心的 东西 ,或者是成长经历里的独特瞬间拿出来, 放 到电影里面,它可能会找 出 一些跟你有相似经历的人,影响到一些人,是一个交流的关系 ,也是刚刚宁浩导演说的那个问题。
提问
想问一下贾樟柯导演,因为我也是山西临汾人,就像您在《站台》当中也是讲述了一代人的经历跟时代变换的过程,在我小的时候我也见证过这样一个时代的转变,因为当时我们家里面也有很多的煤矿,后来一些小煤矿被取缔掉了,一些曾经靠煤矿谋生的人,比如说矿工他们就没有了经济来源。我想问一下贾樟柯导演您是否思考过这样的问题,或者有没有想法把这样子的转变拍到您的电影里面?
贾樟柯:
我好多电影里都有煤矿,最后我看有一个影评人说“贾樟柯离了煤矿会死”,所以我就不拍了(笑),开玩笑。
整个山西省,确实我们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就是山西是一个能源型的省份,确实过去的发展很单一,全省的经济、生活基本上是围着能源来的,特别是在现在这种减排、环保的背景之下,整个面临很大的转型之痛。在这个里面这个“痛”是痛在哪儿呢?痛在每一个山西人身上,经济收入的多少?生活是不是会更容易一些?我觉得这些“痛”,经济的数据跟指标是反映不出来的,它应该是通过艺术才能反映出来。我觉得艺术有一个很重要的跟历史的关系,就是让历史可感。
比如我们今天说同样发生在山西的长平之战,你说它牺牲了多少个人,怎么样的,你会有感觉吗?你不会有感觉的。但是拍成电影你就会有感觉了,你就能够回到具体的历史过程之中。
如果说,我们共同面临了这种转型之痛,而这个会刺痛你的话,这可能本身就是艺术表达的出发点。电影本身跟痛感是有关的,往往你去回忆整个艺术的历史,就算是喜剧,实际上你仔细看它内在都有这种痛感。比如昨天我跟著名“表演艺术家”宁浩联合出演的《地球最后的导演》,里面也有痛感,那个就是徐磊导演在疫情期间对于电影这样一个他热爱的艺术,在疫情的压抑之下展示出来的这种困难所呈现出来的焦灼跟担忧,而它转化出来变成了一部喜剧,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山西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这个故事它有一个情绪点,就是这些痛点。
主持(王晶):
我觉得贾导刚刚讲的这个痛点就是很私人化的东西,因为我们的成长经历都在山西长大,我们会有很多逃不开的主题,像煤矿什么的。但是在同一个主题里面,其实如果年轻的创作者想要找到那个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是可以在主题里面找到更私人化的那个东西,都是谈煤矿的,现在的煤矿和过去煤矿可能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或者你跟这个事情的关系是什么。
贾樟柯:
我补充一句,我觉得痛这种感觉它是伴随着爱的,如果你不在意它,你不爱它,不爱这个地方,肯定不痛,就随它去了,所以它是揉合到一起的。
提问
我想请问一下贾樟柯导演,我们山西从历史一直到现在,贡献出了很多的人才和资源,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可能连我们山西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多贡献,这么强,然后有这么多的资源,无论是现实中的煤炭或者人才、文化等等。我就想问一下您,如何在文艺作品中去输出这样的自信给我们山西自己人?谢谢。
贾樟柯:
我觉得我们经常谈到山西,我想我们在座的大部分都是山西人,我们有引以为傲的历史传统,比如说我们讲,现在身处这个古城是有2700年历史的一个县城,我们山西这样的地方比比皆是,我们有非常璀璨的各种各样的文化。毋庸置疑,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论坛?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发出山西的声音,为什么没有把国际电影展办到广东,没有办到福建,没有办到长三角而办回到了山西,因为山西缺这样的项目。
我觉得整个山西,我们内部说,我们山西人自己讲,我们需要现代化,我们迫切地需要现代化,我们有非常悠久的历史,那是我们的祖宗,我们的父辈他们创造的。但是整个这些资源其实目前来说还在沉睡的阶段,因为我们还是用一个非常传统的、保守的方法去面对世界,而这个世界的发展跟变化已经日新月异,我觉得我们是在现代化的转换中出现了问题。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一方面套用大家常爱说的话,一方面要文化自信,我们确实是文化大省,资源大省。但是一方面我们要非常地客观,我们确实在现代化转化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跟世界打交道的方法。
我就简单说一句,我跟宁导我们的电影中《地球最后的导演》都用方言在表演,我们都很热爱方言。但是我们在跟世界打交道的时候,真的很多重要岗位的领导同志都讲不了普通话,外地人根本听不懂,没有办法,不要说跟国外打交道,跟外省打交道都很困难,所以我觉得需要现代化,从讲普通话做起,诚心诚意地跟外面的世界接触开始。我们不能关起门来说我们山西很牛逼,一说我们是李世民起家的地方,我们是龙城,我们是龙脉,那是几千年前的事情,我话说得重一点,因为我是个山西人我可以这么讲,我觉得我们确实需要现代化,迫切地需要现代化。
主持(王晶):
插一个小广告,今天下午《地球最后的导演》这部短片4点半将会做一个特殊的放映,这个放映除了让大家看到这部影片之外,还要为山西前两天洪水受灾的群众做一个募捐的活动,所以我希望大家不光是电影人,每个观众能以不同的方式去支持一下山西。
贾樟柯:
我说一些我们的痛点,我们山西人有自己的、内部的山西人打交道的方法,处理事情的方法,这些方法不一定能跟普世的、现在通常的、透明的、常规的、普遍的处世方法相对接。很多人来山西做事适应不了,不知道从何下手,最后就卷铺盖跑了,是因为我们从来不愿意跟人家打交道,我们总希望别人用我们的方法来打交道。我们有很多“尽在不言中”,有很多意会,但有很多是外面的世界搞不懂的,人家就走了,人家就到广东去了,人家何必在你这儿猜谜语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相互的,一方面我们要吸引大家来到山西。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试着融入到一个现代化的管理方法、现代化的与人打交道的方法、现代化的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对接的方法中去,用这样的一种态度去打开山西的大门,让更多的人了解山西的美。
主持(王晶):谢谢导演,我们继续听观众提问。
提问
各位老师好,贾导好,我是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的研究生,现在想通过这样一个机会跟贾导做一个简单的交流,在您的影片中一直有山西的文化和精神的呈现,但是随着山西它本身的发展还有您个人经历的这样一种开拓,您认为从《小武》,包括前期的“故乡三部曲”,到后面几个就是近些年来的《江湖儿女》和《山河故人》,近些年来这几部片子,您认为您在电影中对于山西的呈现方式以及对于这种文化和精神的表达,随着您个人经历开拓以及山西本身的这样一种发展有没有一个转变和变迁?
贾樟柯: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并没有太大改变,因为它是两方面的,一个是在创作的时候我的情感方法是基于一个山西人的方法,这个是改不掉的,我们每个人大脑中都有一套“软件”,这个软件是山西给我的。就像宁导拍戏时候要把对白都用太原话捋一遍一样,我写情感,写人与人相处他们的行为方法,思考问题的方法很难免就是山西人的,这个没法改变的,因为我确实在山西生活了23年,血统里面就是这样一个人。
但另外一方面我并不觉得山西在我的电影里占有特别大的重要的位置,因为我把山西当做一个普遍的世界来看待,并不觉得它有一个所谓非常独特的地域性才去呈现它,而是因为它的普遍性。我觉得写山西跟写河南应该没太大区别,都是写人。我跟山西的关系“又在又不在”,所谓“在”就是我在,因为我是山西人,情感方法是山西式的,“我不在”是因为我讲的就是人,我不觉得我电影中只代表了山西人的经历跟经验。从这个角度来说并没有太多自觉的意识说我在讲一个山西故事。
我们平遥国际电影展有一个单元是山西本土创作,没有叫“山西制作”或者“山西创作”,我们叫“从山西出发”,我们出发是从这儿出发的,带着我们山西给我们的世界观、情感方法出发的,但是我们接触到的是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提问
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先问一下宁导,您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太原人,我很好奇你的成名作,像毕赣导演、李睿珺导演他们的处女作或者成名作都是自己出发的地方,但是您的第一部成名作算是《疯狂的石头》,是在重庆,您当时选择重庆的理由或者出发点。第二个问题想问一下袁媛老师,我刚才听您的谈话中听出来一点,您在早期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彷徨和无助的,您现在至少是在电影这个圈子里,也非常有成就,我特别想知道您当时彷徨和无助的那段时间是怎么过来的,还有您的一些想法,对于正在处于这个阶段的人的一些建议。
主持(王晶):
我有点好奇比如说您刚才提的“太原往事”,您准备做的这个电影,这个点子是从您一开始做电影的时候就在心里种下了,还是说经历了这些之后再回看,你觉得你看得更明白了,跟那个观众的问题是一样的。
宁浩:
这个剧本其实我构思了得有十几年了,以前一直想写一个尖草坪那片儿的一个故事,因为对那个地方很熟悉,但是其实已经写过一遍就放下了,就觉得离自己太近了,我还是想再去观察观察它再拿出来做,所以一放就放了十年。我的第一部电影其实不是《疯狂的石头》,第一部电影叫《香火》,是在大同边上的一个县城怀仁县拍摄的。我前两天还路过怀仁县,我发现那个变化非常巨大,从远处看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现代化的楼群,那个变化非常大。
但是我会发现山西的变化是这几年的变化特别巨大,其实前面的时候,二十年前,十多年前它的变化还是比较缓慢的。刚才老贾提到我们要快速现代化并且拥抱现代化的这个观点,我觉得其实是特别好、特别对的。就像你问我,当时在选择《疯狂的石头》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放在太原拍摄,因为在当时那个时候,客观地说太原的现代化程度还支撑不了一个电影的拍摄,在它那个生产当中是比较有困难的。
所以,虽然我写的都是太原的人和事儿,但是我觉得反而是还不能够简单地搁到太原就可以了,那个就显得太粗暴了,或者本身对电影也不太负责任。所以就把它进行了“异化”处理,虽然都是写的太原人、山西人的精神风貌,但是我把它变成了一个重庆的方言,放在重庆那样一个更丰富,更加零零总总的城市里。但是太原整个渗透出来工业城市的氛围,其实是一直放在我心里的,我当时很想有一个作品把它给呈现出来,所以我现在正在写《太原往事》。
主持(王晶):
多问一句,您刚才提到您第一次写完《太原往事》之后觉得这个东西离自己太近了,那个“近”是什么?
宁浩:
我总怀疑我自己,当我写我自己身边的人和经历过的这些事儿的时候,这个视角其实是并不客观的,就很容易被自己欺骗,那一点我其实也是蛮警觉的,我一直希望我能够再成熟一点再来反观这个事情。
主持(王晶):
其实都是我们从山西出发去看到更大的世界,再回看我们,再一遍一遍检视自己的生活。
宁浩:
对,我其实一般在处理一个故事的时候还比较“冷血”,比较理性,不是非常地感性投入。所以我还是希望我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姿势吧。
袁媛:
关于青年创作者的必经的一个阶段就是彷徨不知所措,对自己产生了极其强烈的自我怀疑,会认为自己是不是才华不够,所以不适合这个行业。我觉得基本上所有的青年创作者都会经历这个阶段,这个阶段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帮得上忙、最终只能靠你自己度过的难关。我当时最摇摆的一个阶段就是在《滚蛋吧!肿瘤君》做编剧的前一年,那是我最焦虑的一年。因为已经毕业有五年还是七年了,一无所成,所有自己做过的项目没有一个能够(成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失败了,那个时候一定会产生强烈的自我怀疑,会认为说是不是因为我的原因所以这些东西全失败了。
那段时间我碰巧看了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这篇小说,那个小说给我的触动非常大,我觉得那个小说出现在了我自己的人生中最迫切需求精神支柱的一个阶段。除了这个小说它给我的力量之外,当时我也求助了宗教,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单靠一个人他自己的精神力量很难支撑自己的精神世界。在面临垮塌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一种力量感的东西去支撑的话,毫无疑问会一下子就把一个人击跨的,我必须得向外界求助,但这个外界不可能是任何一个人给你力量,也许是一个团队,也许就是一个和你境运相同的一群人可以在一起抱团取暖,但是到最后你是否能闯过这一关还是要靠自己。
有一个人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 这个行业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人,最后都是这些人自己选择离开。 江志强江老板也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你只要还在这个赌桌上你就有胡牌的可能,但是你一旦离开就永远没有这个可能了。不知道能不能帮助到你。
主持(王晶):
大家都很热情,但是今天时间有限,希望大家可以攒着,因为我们在平遥,电影人相聚在这儿,我们相信大家每年都会回来的,大家可以每年都见到,大家聚在一起。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想请每一位在山西生活过、创作过的导演们留一句寄语,跟故乡再说一句话,跟电影展、跟平遥都可以。
宁浩:
平遥国际电影展现在是成为了我每年回到故乡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理由, 我希望能够年年都回到平遥 国际 电影 展 来,来看看家乡的父老 乡亲 , 来看一看家乡的变化。
李睿珺:
到平遥的时候看到有那么多年轻的面孔,大家在热烈地讨论电影,最近一段时间因为电影的问题会比较焦虑。 但是看到那么多更年轻的面孔的时候,你又重新 地 坚定了自己继续出发的勇气。
毕赣:
我是第一次在国内的电影节展来玩,这次就特别地开心,因为我们那个单元 看到了好多各种各样国家的电影,对我非常受用 ,以后就经常来,也 希望大家每年都在这相聚 。
韩杰:
我是这几年回来得越来越少,一是疫情,二是工作上的高强度、高密度的时间安排,所以我自己都很少回来见父母,基本一年一到两次。但是心里边一直有故乡的厚土,这个厚重是一直在我心里头,我自己都觉得我越活越像一个山西人了。 你们如果是山西的年轻人 , 那就多出去看看,多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也提醒自己多回来山西看看。
袁媛:
我是希望将来不仅能以一个山西籍导演的身份出现在平遥国际电影展上,还希望能够带着作品能和在座的各位有更多、更深的一些交流。我坚信我将来一定会写山西故事的。
大飞:
希望以后还能有更多的机会来创作山西故事,拍摄山西的影片,跟大家一起交流,谢谢。
贾樟柯:
坚持把平遥 国际 电影展办好,每年服务大家,让大家能够相聚在山西,相聚在平遥。 山西首先得我们山西老乡自己建设。
韩杰:
去年贾导面临了很大的举办平遥国际电影展的压力,大家也都看到新闻了,我当时给他写了一段文字发微信给他,我说这个电影展除了你别人都很难完整地干好、并且干下去;我说将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愿意鼎力相助,我希望平遥国际电影展还是由你来办。结果今年又正常地回到了轨道。我特别感谢贾导我的师傅,也希望电影展越办越扎实,越办越受大家的欢迎。
主持(王晶):
昨天电影展颁奖仪式结束以后大家在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发现好多人跑到走廊里面来,我说为什么大家都出来了,所有人都说太热了。那个“热”,我相信不是因为空调开得太大或者喝了一点酒,我觉得那个热其实是心里面的激动。 我最大的感受是今年来平遥 , 一部好的电影会让整个夜晚都变得非常 地 美好 ,平遥除了我们来相聚,它更多的是一个聚会,是一个 party ,也希望每年大家都能来这个 party 。
我们今天的论坛到这里就结束,谢谢大家。
2021PYIFF学术活动【对话】在山西生活、学习、创作-嘉宾与观众合影
-------平遥国际电影展-------
平遥国际电影展(Pingyao 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创办于2017年,每年于拥有2700年历史的平遥古城举办。前四届电影展已于2017年至2020年成功举行。
在展映世界各国优秀影片的基础上,平遥国际电影展尤为注重发现并积极推广新兴及发展中国家青年导演的优秀作品,为这些影片提供发声的平台,旨在增强世界各国电影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以激活、繁荣世界电影的创作。
平遥国际电影展以“卧虎藏龙”为名,由电影展映、产业、学术、教育四大板块构成,其中电影展映板块包括卧虎、藏龙、首映、回顾/致敬和从山西出发五大单元,产业板块由发展中电影计划、平遥创投、平遥创投·剧集计划等单元组成。